Abstract:
Due to the unclear basic data, unclear control rule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various historical problems,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jointly organiz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the pattern of marine ecological secur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system in China, the mai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of the adjustment, which are expected to serve a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ies related to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zoning and manag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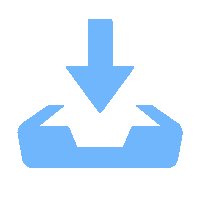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